回家前,我常喜欢跑去火车站的超市走一圈。小城没有什么夜生活,大部分的地方一到日落,就再没有人的气味,一群中世纪建筑栖息在一起,生命的味道随着余晖逐渐消散。火车站是唯一的例外。骑自行车逐渐迫近那里的过程中,生命就逐渐地扩张起来了,像是一种生育的景象。
城市里和我一样的夜行者都聚集在那里,一来有人火车通勤,二来火车站也是市内公共交通的中心,三来,火车站里面有唯一在日落之后还营业的超市。教堂的钟声将虔诚的人送回了家,他们乘着日光,在热闹的超市里买齐家居百货,而夜幕低垂时,所有顽皮的上帝子民都聚集在了火车站的超市中,好像最终的审判在每天都重复一次。
进入超市要从车站穿过,因为它在铁轨的另一边。夜晚车站的怪人和超市的略有不同,他们怪得更潇洒,更坦荡一些。每个星期的某几天,第十五站台边的长椅会坐着一位穿着恨天高的女人,她的头发剃得精光,手里拿着深色提包,穿一件轻量羽绒服。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她的打扮有点诙谐,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第二天,她还在,第三天,还在。第四天,她不见了。第二个星期,她又在那条长椅,一样的高跟鞋,提包和羽绒服。我常常会有点害怕,这世界会不会是神仙导演的一场戏,由于演员不够,所以常常要重复使用。每次见到她的时候我都在想,也许不仅演员时有或缺,连道具和妆发也都是条件有限。
火车站的固定人物还有几位,在门口杂耍的男人是另一个经典。他每天都会在火车站门口丢一个饼状物,那饼从他一只手中飞出,掉落在他手臂半径的任何一处,而另一只手永远可以精准无误地接纳掉落的饼,如此循环往复。那只饼一定是小城每一个人都见过的一块饼。杂耍男人的脚下有一只用于承接捐款的碗,一碗一饼,就是他所有的劳动工具。他虽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但我从没见他缺席过哪一天。只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鹤立从英国来看我,我兴致勃勃地想跟她介绍杂耍男人,就像景点一样。但那天他却没有在那里。我不知是否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但他好像并不愿意我将他介绍给游客一样。似乎他在用行为告诉我,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公仆,为小城的居民提供自己能给予的娱乐服务,没什么好介绍的,“就请让我在历史中被忘记吧!”
车站外部,有很多供人休息的长椅,日积月累,那里已经不再是游客的地盘。爱喝酒的人们聚在那里,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眩晕的状态。我常见到一对情侣常坐在其中的某个长椅上,男人拉着手风琴,声音悠扬,悦耳,总让傍晚回家的我感到一阵怅然。有一次,我低头看他的脚下,那里没有碗,他没有在卖艺,也没有在行乞。他只是坐在那里,喝酒,拉琴,和女友共通度过落日余晖洒在地面的傍晚。
我听说,如果一个人是瑞士的公民,那么即使不去工作,政府的救济金也可以让人过上很舒服的生活,只要保证定时向政府证明自己在努力寻求就业,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常在想,在火车站扔饼的男人,他愿意这样做吗?只需定期告诉公职人员,我在努力让自己成为工具!就可以拿到让人不需要扔饼的工作,他有去做吗?或者说,为什么我会认为扔饼不是一种职业呢?我的视野到底有多小呢?
也许,我也是火车站的一景吧。一个亚洲的女生,每天推着自行车走过车站,常常莫名地唱起歌来,她来这里做什么呢?为什么她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呢?她心里在想什么?她是不是从没读过尼采和亚里士多德?
为什么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天色渐晚,落日西垂。又到了去火车站超市的时间,今晚,我可以买到恰巧打折的火腿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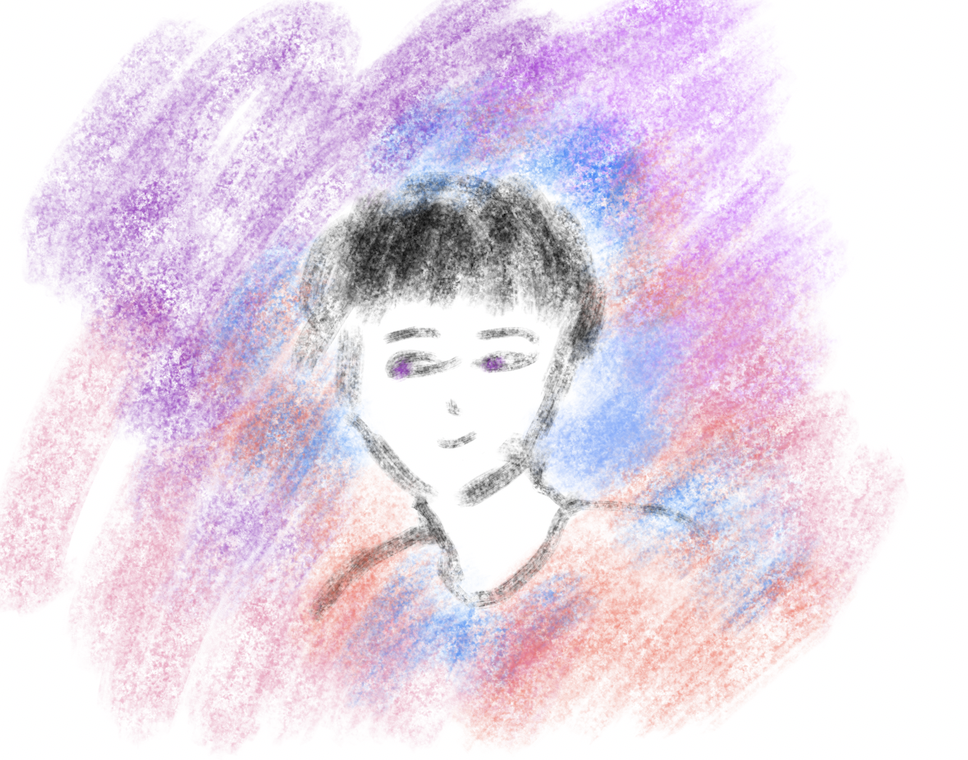
我出镜了。扔饼哥第二天疑似现身了
我name dropper
要不要来格鲁吉亚🇬🇪逛逛
格鲁吉亚得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