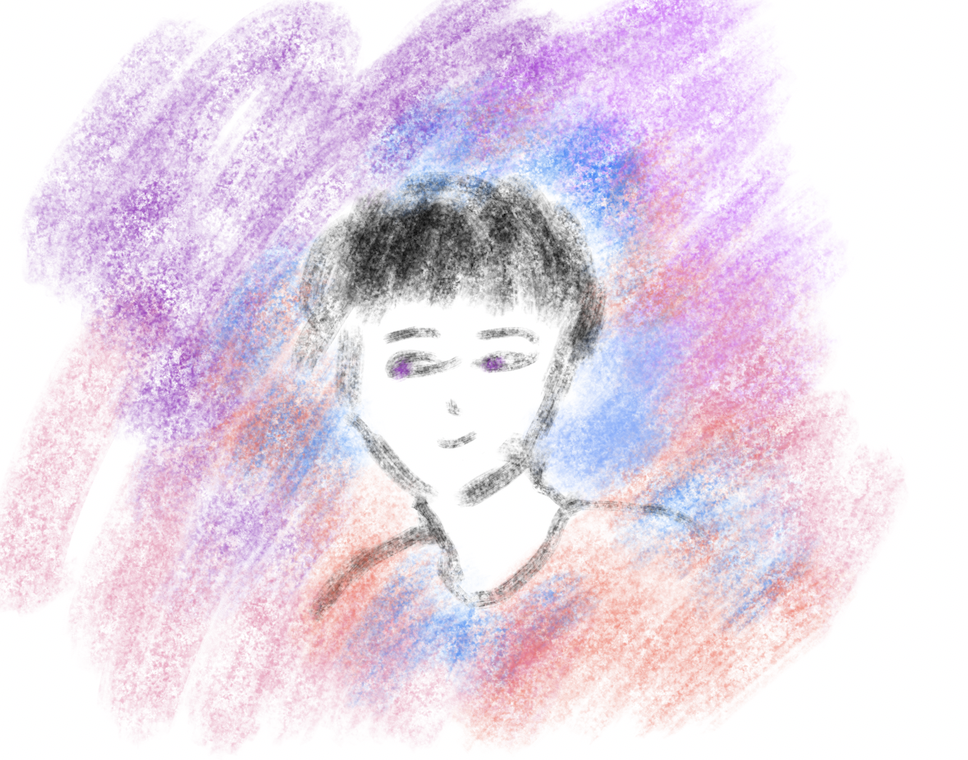虽然常常吐槽瑞士,但是这里有很多制度和文化让我叹为观止,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是常常感到一些惊讶时刻,让我对很多事情产生深久的思考。
体会最深的自然是教育。这里的本科录取对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开放,只要通过高中毕业的测试,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学校和职业。公立大学几乎没有学费,但教授的资历和学校的设备及馆藏的书籍水平极高,是政府的资金支持。本科生和部分硕士生是双专业学制,此外有固定的学分配给每个学生自由地选择课外的专业,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学生在一到两个学期之后会在选修课或第二专业的课堂中找到自己更感兴趣的专业。大学转专业非常灵活,甚至学校鼓励学生在探索之后不断调整专业,以确定自己真正的兴趣。热爱是专业对学生的最大要求,而并非擅长,虽然后者也很重要,但并非首位。学生自然需要通过课程才可以毕业,但专业吸纳学生的动力来自自主性,也就是agency。反观自己的成长经历,不论是自己还是周围的同龄人,都是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而这擅长,常是小时候老师或者其他成年人的一句话而已。“这孩子是个苗子!”就定位了ta在某个领域的一生。
这样的教育哲学是一种对人的尊重,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发挥自己想发挥的天赋,而不是做得最好的天赋。这样的体制可能在“竞争”中并不是最好的策略,但这取决于对世界本质的解读。如若认为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那么社会的组织基础就是最大限度地防御敌人和发展器具,这样自然会产生以能力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也就是以每个人最强的部分来决定ta的事业。但如若对社会的本质理解是通过共同努力发展出和平共处的方式,一同创造人类的文明,让每个生于社会的幸运之人有空间发挥自己的才能,做自己想成为的人,而非更好用的人,那这样的社会是会鼓励“ta想要”,而非“ta会做”。
本系的本科生如果能完成一篇初级论文,就可以选择修硕士的课程来满足本科的学分,因此,我有很多本科生朋友,有的好友和我的年龄差有近十岁,但令我意外的是,ta们常让我有同龄人的感觉。这种成熟自然不是混迹过社会的油滑,而是对待生命有成熟的判断力,知道何为好和善,接受人的复杂,但努力向善。同时,她们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知道如何控制收支,了解营养,热爱运动。在童年的教育中,学校会教授很多认识世界的课程,从基本的能力如做饭、制作器具和艺术品,到了解城市生活中的一切从何而来。我认识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他的职业是本地制盐公司的导游,常会带学生或成年人小群体参观工厂。当时我对他的职业很惊讶,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去看盐的制作过程?现在我意识到,为什么那时的我,会认为人可以不知道盐是怎么做的?
起初,我发现瑞士有很多女生喜欢手工编织,我有些不以为然。在我的心中,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一定不是一个喜欢织围巾的人,甚至,我在国内时刻意不愿意学做饭也是这样的原因:我有一个对独立女性的刻板印象。后来,我读了一些数据,意识到性别更平等的国家中,女性反而可以自由地选择那些有“女性化”标签的爱好和职业。自而反思自己,为何会认为可以满足温饱的物品不值得投入自己的时间?
本地对于“物”的态度,也让我有很多体会。起初,我很不适应瑞士人对物品的珍惜和维护,那时,我对工具的态度很轻蔑,这也是我自己对某些概念的刻板印象之一:我曾认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应当反抗器具的暴政。那时,我很不习惯在这里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护自己拥有的一切物品,清洗、维修、整理、分类,小心翼翼。但在我后来的反思中,我想到自己对于物质文明实在太想当然了,工业化生产让我忘记了材料和制作的来之不易。另外,人的工具就是人的延伸,好的工具可以让人忘我地创造,我想,花时间去维护好的工具,是我对它们基本的尊重。
瑞士人很喜欢用纸,好友常在路过我家楼下的时候,在我的信箱中投入一张手写的卡片,日积月累,我已经有了一小叠她送来的卡片和信件。由于家庭的变故,我曾丢失了大学前所有的物品。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曾故作潇洒地认为,对物的留恋是应当学会舍弃的,这样才能做一个精神上更自主和强健的人。但这样的想法自然是有问题,因为物是可以打开回忆的中介,当我的头脑将部分回忆忘记之后,只有看到物品才能想到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这是对人的经验的保护,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保护。
对于垃圾,在这里要分成近10类。起初,我很烦恼。但后来意识到,这件事其实十分简单,因为标准的细致和准确,每个人都可以迅速地找到每一个包装的处理方法,而在熟练之后,会意识到大部分垃圾都只需要分成3-4个大类,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除却一开始学习的时间,此后每天只需要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维持这样分类的生活秩序,但对环境的保护意义又有极大的好处,是造福后世一种行为习惯。我想,这是因为制度的制订者花了很多的心思来简化和精细化流程,才减轻了市民的工作量,让大家都有动力坚持去做。毕竟,每个人都想做一些好事,如果这件事被设计得简单又优雅,大家就更愿意去做。
这里的制度很在意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责任,这是我刚到学校的那一天就意识到的一件事。那天我去学校领取入学材料,需要填写地址和联络方式等信息。在把材料递给工作人员后,他强调了一句文件上的话:如若你改变了地址或个人信息,那将这些变更告知学校是你的责任(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do it)。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常常出现,我留意到它,因为它的语法很特别,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这句话的重心在于责任,这种哲学与大学的教学原则是一体两面,都强调个人的主体性,让每个人能意识到,这场生命归根结底是自己的责任。
我常很意外,也常感到很愉快,能在一个和自己生长环境迥异的国家里,去学习和反思,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